《王的盛宴》工作照
在拍摄和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我慢慢地看到了自己心智的边界,我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么大一个话题的时候,自己已经包不住了,没办法通过理解、吸收、发酵,最后留下那“二两酒”。——陆川
当陆川有兴趣去关注秦末汉初那段历史,他发现,真正让他兴奋的不是在民间传说或者民间戏曲里众人皆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不是鸿门宴,不是乌江自刎,而是最终的胜利者刘邦内心的恐惧。他开始翻读《史记》,查阅史料,采访历史学家,试图从中得到答案。所以他没有接拍后来由香港导演李仁港拍摄的那部《鸿门宴》,而是重新去写一个故事,还原那段历史。从因权力而恐惧这样的角度去拍古装片过去还从未有人尝试过,陆川希望在《王的盛宴》里把它讲出来。
这种兴奋或多或少让陆川在随后的操作中有些失控,一方面他希望呈现出一部历史片而不是古装片,另一方面他的文艺情结又干扰了他叙述故事流畅性。当一部三段式的电影送到电影局之后,他得到的回复是:你是想拍一部电影还是想拍一个影像书?
陆川拍到第四部电影时,终于遇到了麻烦,他必须从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为此绝望过,甚至不想再去看一眼。在过去的半年,陆川像是做了一场噩梦,然后他忽然悟出来,其实刘邦何尝不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呢。这样,他再次鼓足勇气,重新剪辑了《王的盛宴》。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次拍电影中间都会遇到一些波折,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在审查上遇到了一些麻烦。
陆川:可能不光是我一个导演,中国很多有代表性的导演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冯小刚[微博]、张艺谋、宁浩[微博]……只是这一次轮到我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要面对和你内心意愿相违背的事实时,你怎么来调整和接受这个现实?
陆川:这种事情让人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压抑,这种挫败感很强。但好在这是一个过程,《王的盛宴》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至少它还是我当初想做的那个东西。中间停下来的那几个月,没有浪费,虽然经历了十几个版本的修改,有一些我很在意的点被迫拿掉,但最后的这个版本还是完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了应对审查,在不停地修改?
陆川:是的。我从来不认为审查是几个人的事儿,这是整个社会的事,是几个人在代表体制发声。我也在想,当时有些东西是没有做好,那就是电影本体,电影的叙事层面,不像一个完整的电影。所以,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电影的叙事层面努力,让它平顺了,看起来更像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写剧本的时候,没有考虑从一个叙事角度来写吗?
陆川:最初的剧本很长,故事性还是很强的,但在后期拍摄的过程中有些纠结,应该说现在这个电影完整地记录了我的迷茫。我会特别想弄明白一些事情,比如韩信为什么会离开项羽,这件事纠结了我很长时间。当时我设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韩信是奸细,另一个是韩信在跟着项羽进宫的过程中自己的野心也在膨胀,这些都是在文字和分析上形成的逻辑。但真的到了电影开拍的时候,就又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是韩信的野心膨胀了他就应该跟着项羽,为什么他要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项羽去投奔落魄的刘邦?那个时候刘邦处在一个被发配的境遇里,每天几千士兵的流失,一二百名将领逃跑,他当时就是一个流落于西北地区的丧家之犬。有些史学家的解释是,项羽不重用人才,但我觉得即使再不被重用,一个人也不会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跑去中非的某个国家,即使再有雄心壮志,这个逻辑也是不成立的。我最早的构思是韩信是奸细间谍,但最后我没有用这个构思。事实上,间谍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但如果按这个方向拍,这部电影就会成为一部“无间道”。如果把那么大的一件事又讲成了兄弟情,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所以最后我对这个问题就基本上没有解释。但我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是,我还是在电影里还是稍微回忆和分析,我最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完全不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那为什么还要纠结呢?
陆川:我心里一直有个声音说这样拍是不行的,我要拍的是一个主流电影,要拍成《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教父》那样的电影,必须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如果去拍那些具体的事,它们无法指向我最终要表达的意义。那些故事太精彩了,以至于一场“乌江自刎”就会让你忘了这个电影的意义,你全部会被项羽吸引过去,他的死就是英雄的、感人的,你不会再想到其他的意义层面的东西。所以,我只能从这些故事和关系中间找到最有兴趣的点来拍。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我不知道这部电影上映,当普通观众、“90后”观众、女性观众面对它的时候会不会和我一样激动,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拍这个题材?
陆川:当时拍完《南京!南京!》之后并没有选择这部片子,本来是要拍《英格力士》的,但那个本子一直没有通过。那时候正好星光国际找我来拍《鸿门宴》,作为男人我还是很想拍骑马打仗的戏的。因为我是编剧出身,所以我的习惯是拿到剧本之后先去看书,把《史记》里相关人物的列传、本纪都看了一遍,又翻了翻《资治通鉴》和一些专家写的分析类的书,包括李开元、陈景元这样的史学家的书。《鸿门宴》是完全按照反间计这样的套路来讲的一个故事,当然情节很紧凑,但这与我在看史书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冲动和兴奋相比就有些小了。而且我反观那些看过的书,其中最让我触目惊心的就是刘邦杀韩信。你想想,历史上赵构杀岳飞,崇祯杀袁崇焕……所以这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典型案例。书上写处死韩信的罪名是:纠集家奴和街上的流窜犯夜袭皇宫,企图杀害太后和太子。当时告发这件事的是韩信的家奴,司马迁写到的家奴告发韩信的原因是他和韩信产生了矛盾,韩信要杀他,家奴逃跑连夜进宫告密韩信谋反。我们知道这样的常识,在法庭上,这样的证人提供的证据是不能采用的。司马迁很聪明,他把这个大前提写在最前面了,所以后面的东西是否可信完全由读者评定。当时我在写剧本,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所以我编了一个年表。这个表的横轴是刘邦、项羽、韩信、吕雉、张良、萧何、嬴政,表格的纵轴是时间。也许这个表格对于电影的用处很小,但对于我了解这整个事情的帮助太大了。当我把这个表格列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很多巧合,比如刘邦和韩信在薛城第一次相见,同一年他们俩一起投奔项羽,项羽给了刘邦五千兵,收了韩信做侍卫,这些我都拍在电影里了。还有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事情,是要靠数据和时间来表现的。比如,项羽死后的第二天,韩信就被剥夺了军权,30万人的军队全都没有了,第二年就在云梦被逮捕了,原因是觉得他可能谋反。从第二年被逮捕,一直到刘邦死前半年,韩信都被软禁在京城里,一步未出过京城。所以,他不可能有很多家丁,不可能去夜袭王宫。我突然明白了,司马迁在《史记》里藏了一些事情,再加上和被称作“史学家的福尔摩斯”李开元教授的沟通谈话,我在这方面有了更深的体会。应该说,正是和李开元那次谈话之后,我决定放弃拍《鸿门宴》了,因为《鸿门宴》就是按照《史记》来拍的。鸿门宴这段历史,司马迁采访的是樊哙的后人,司马迁的女儿嫁给了樊哙的后人,所以鸿门宴里樊哙的角色会显得很重要。事实上,樊哙在历史上并没有特别显赫的军功,最大的功绩就是一直陪伴着刘邦,是他的乡党。以当时95%的文盲率来说,樊哙可能是一个文盲,但在《史记》里记载的樊哙说的那番话并不是一个文盲能说出口的,历史的记载是有偏差的。刘邦杀韩信这件事在我心里成了一个心结,因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类似的事儿,我特别希望通过一部电影来讲刘邦杀韩信,这件事成了我拍这部电影的唯一动力。但这个动力又让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特别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走才能走到那儿,才能讲清楚这个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史书和历史学家在你形成剧本过程中思路上有什么帮助或者改变吗?
陆川:在这条路上我遇到了两种专家,一种专家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比如陈景元。我看完他的一套书后去了一趟陕西文物博物馆,去拜访了他的对手,对方也说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后来我知道陈景元的书也是有局限的,他选择了对于他能形成完整逻辑链的故事,但不在他逻辑链里的故事他就没有放进去。真正有实力的大师是能把双方的东西糅在一起,还能保存疑问,而且总结出的观点解释相互对立的观点。陈景元那本书给了我特别大的感动,他是一个半业余的历史学家,却能撼动历史学界,而且里面的很多东西专业人员都反驳不了,他仅仅是一个人在研究,他的理论已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也给了我很多提示。第二种专家是像李开元这种,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中国历史,对于《史记》我们俩都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他是有研究的,我是无知的,我只是觉得这里有问题。他是做过田野调查的,他可以告诉我答案。所以我觉得如果电影也能在这上面做一些东西会很有意思,历史是不是可以逼近?杀韩信时我们没有用他在长乐宫被砍死的记载,也没有用传说中的三步杀,我们用的是绞死。电影里关于这方面所做的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是挺顺利的,也很扎实。但是在电影本体上,我还是很迷茫。我其实自认为是很懂电影本体的,觉得我是可以把它做得像《教父》一样,东西全部藏在故事里面,那种艺术是若隐若现的,普通观众能享受到一个非常丰盛的故事,但它还会有其他的价值需要被读解出来。但是拍摄过程中探索让我感兴趣的东西的想法太强烈了,结果故事沉底了。我不认为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古装片在细节上都比较粗糙,而你却花很大精力去还原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可支撑的史料并不翔实,那么你向观众还原哪种历史感呢?
陆川:我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首先我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同时一定也是一个尖刻的批评者。所以我特别理解网上很多电影爱好者的尖锐的批评,因为自己也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很多的批判是针对古装片的,我在看很多古装片时也会觉得不过瘾,会挑毛病。比如,这部电影中关于马镫子的讨论,我觉得我已经对电影的要求很高了,但你会看到很多观众还是保留着敏锐的批评的态度。马镫子的那个细节,在我们很多出土的文物里,包括兵马俑都没有马镫子的实物。我们有一个演员叫老莫,他是哈萨克族的,这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我曾经让他练习骑射,练好了之后教给所有人。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马镫子是没法把握平衡进行骑射的,但那个时候已经有资料记载项羽是有轻骑兵的。我也咨询过历史学家,他们承认如果没有马镫子不可能在马上打,但轻骑兵突袭的时候一定不会骑到地方了下马打仗,那就失去了突袭的意义。我们看那个年代出土的文物,青铜器、百戏俑……马镫子和这些东西相比是太容易制作的东西了,只是那个年代金属稀少,可能它是用其他材料制成的,没法保存到今天。没有马镫子是没办法解决支点问题进行骑射的,所以我们就在想也许当时有和马镫子类似的装置,所以我们最后选择用两根皮绳充当马镫子。
类似的这种事情我们做了很多。还有复原鸿门宴,是从项庄这个点向外推论的。我们研究项庄舞剑的活动半径,它应该不是像《江南Style》那么大的活动范围,项庄舞剑可能是一种很仪式感的东西,但他在跳舞的过程中能够屡屡地伤及刘邦,这说明活动半径不会太大。那时候铁剑和青铜剑的长度都是固定的,铁剑有110或120厘米,青铜剑太长会折断,所以最多也就是90厘米。我们根据这个量出了五个人座位之间的距离、面积,然后再去判断榻的大小。如果你是皇帝我是臣,我们面前放的豆的数量是不同的。豆的数量决定了案几、石案的大小,石案又决定了下面座榻的大小,宴席上榻的两旁还有两名侍女服侍,在剧中我们给刘邦安排了一名侍女,因为他的地位还不够。还有就是上下菜时的流线图,我们排练时用了100个北京演艺学院的学生,穿上我们的服装在帐篷里面排练鸿门宴,排练端菜、出菜的过程。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排练完之后,我们发现无论怎样樊哙都出不来,通过这个排练你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刘邦能跑掉,没有任何原因,就是项羽放他走的。我用100个人去排练这场戏的时候就不用我去说这事,所有人都明白,一定是项羽发令的。所以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些事情,不过这不解决叙事的问题。我们在这条线上感觉很顺利,在感觉越来越有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故事的假定性特别强,那种假定性和真实性产生很大冲突,所以在发展故事的这条线上就越来越困难。樊哙出来指着项羽骂这是在剧本里写到的,但排练完了之后你觉得骂不了那些话,拍起来是不合逻辑的。之前的很多戏比如项庄一伸剑转两圈就能刺到刘邦,这些事都需要精确的计算,拍起来就特别舒服,只有樊哙冲进来那场戏感觉特差。这对于以前的古装片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对于我们这些“技术控”来说就不行,所以后来这些就都删掉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带着答案去拍的电影,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拍,但做着做着给自己做蒙了的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古装片大都以娱乐为主,但你在追求一种真实,真实的代价可能是它并不娱乐,你刚才也在担心很可能年轻观众会看不明白,他们很可能奔着吴彦祖[微博]或者张震[微博]去看,但看完之后会觉得这不是他们想看的片子。
陆川:娱乐性这件事我没有有意地拒绝,我还挺喜欢的。拍《南京!南京!》我觉得我能控制住题材对我心灵的影响,但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控制不了,它会慢慢侵入你的内心。最初我就是想拍一个《勇敢的心》那样的至少还是主流的片子,但却说了一个很博大的事。在做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咱们中国历史中供你解读的素材会让你沉重起来,这种沉重实际上是我想去挣脱的,但它又无处不在。因为你对于过去和现实的联想每一天都在,而我又不愿意去借古讽今,因为今没有什么可讽的,古书上全写明白了。我只是想说拍一个历史片,把这个规律说出来,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去摆脱这个禁锢,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可能每个导演对一个故事的解读都和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你的每一部电影都在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这个“沉重”是从哪里来的?
陆川:其实我不是特别愿意说这些事情,因为如果要说是可以说出很多东西来的,而且这其中的很多东西我是希望留给自己的,把它们作为燃料推动自己继续前进。就像酒开了瓶儿一样,气儿散了没有味道了。而且我很怕以后人们按照这些东西去解读我的作品,那就显得没有味道了。回想一下,我的人生在拍了《可可西里》之后,拍《南京!南京!》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几个因素促使我拍了《可可西里》,首先是我出生在新疆,其实我是一个新疆的孩子被扔到了北京广播大院儿里。前几天马东采访我,当年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他每天绑起来一个孩子然后假装枪毙他,他绑起来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我们现在的关系很好,但当年我几乎不和他们一起玩。到今天我一直没有拍都市题材的片子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对城市的那种认同感。后来我念军校。这些经历让我有一种叛逆情绪,是促使我去拍《可可西里》的主要动力。拍《南京!南京!》之前进行的超长的准备工作是我在文史知识上的一次积累,这种积累让我突然认识到曾经我们受的教育是有偏差的。从《南京!南京!》开始,我阅读和积累的东西是海量的,整个日本人和我们交战的过程到后来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屠杀的历史我都研究了一遍。这些历史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我原本的那种冲动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一种叛逆,但这种叛逆没有知识结构的支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对国家历史的正确认知。但同时我也发现,这种没知识不只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王的盛宴》是我电影青春期的一个句号,我很高兴自己电影的青春期在这里结束。如果说《王的盛宴》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没能把它拍成像《教父》一样牛的东西,让读者可以停留在各个层面上理解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剧情和文本层面是完善的,在意义的表达层面也是可以的。我的成长经历和我对那些历史的研究让我觉得如鲠在喉,它吸引了我所有的目光。我希望可以拍一部历史片去讲历史,历史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积累了两千多年的财富,我们没有好好地去经营它,没有拿到该拿的那笔利息,干的大多是砸银行的事儿。我想看看这一次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提点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王的盛宴》是你电影青春期的句号,这次对你有什么触动和改变?
陆川:当时写剧本的时候面对的故事和选择太多了,这种取舍是特别难的,我无法判断哪些是更有价值的。刘邦的恐惧其实就是一句话,我如果在剧本里反复写刘邦害怕、恐惧,这个剧本写出来之后就显得装神弄鬼了,你不会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哪一场戏都有动态有视觉,哪一场戏不比刘邦的恐惧要精彩?这些用文字创作的时候是看不透的,所以我都写下来了。在拍摄和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我慢慢地看到了自己心智的边界,我发现自己在面对这么大一个话题的时候,自己已经包不住了,没办法通过理解、吸收、发酵,最后留下那“二两酒”。这“二两酒”是在创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慢慢找到,是经历了一个纠结、试验、反复思考的过程才找到的。我不相信有哪部好片子在创作的一开始就是非常完备、设计精确的,我相信所有的好片子一定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片子后来一直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动摇或绝望?
陆川:其实一度我觉得这部电影要完了,拍砸了,想说的事没说清楚,甚至觉得这是我的滑铁卢。曾经我一度连看都不想看,因为每一次看片我都觉得非常痛苦。当初看《南京!南京!》,每一次看我都会哭,但每次看《王的盛宴》我心里都特别难受,有一段时间这部片子被我完全搁置了。但现在,虽然我觉得这部电影也许在商业上依然有问题,但对于它存在的价值我是非常坚定的。当时悲观的想法是,之前三部戏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可以继续拍电影的努力可能都要因为这一部戏完蛋了。在把这部戏搁置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鸟巢”的演出,这完全是出于宣泄而做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意外地收获了一些制片管理的经验,也意识到,我心里有很多疑问等着我去解答、去面对。所以在“鸟巢”演出基本上做完的时候,我又回过头去重新看这部电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是我花了48小时没有睡觉剪出来的,我觉得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给这件事一个交代。那48个小时我在机房里突然就明白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了。即使后期剪出花儿来这部片子也变不成《教父》,变不成《现代启示录》,只要坦诚地露短就好了。之前的三段式很文艺腔,不容易露短,现在这种结构是在讲一个故事,很容易把短儿给露出来了。这个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在第四部电影里露了短儿,下一部戏要想得更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的三段式为什么你觉得不行呢?还是广电总局觉得不行?
陆川:当时广电总局讨论的时候就觉得三段式不是一个完整的电影,是一本影像书。原本的三段式的嵌套解构,它的作用在剧情上,而我拍的三段式更像是一个有因果性的证论。
三联生活周刊:你把三段式的结构打乱了,最后剪成了一个故事,拍的素材能够支撑突然的变化吗?
陆川:当然应该再多几场戏会更好,但现在看起来也还可以。但其实多拍几场是好是坏也不是非常确定的,因为如果这个口子打开了,那很多戏可能都要拍,那要想的事情就更多更纠结了。所以我现在不愿意去想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现在终于结束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真的是噩梦般的一个经历。
三联生活周刊:三段式的版本倒是能让我看到萧何和张良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命运,你在拍的时候,对历史上士大夫的命运有过思考吗?
陆川:当我在看《史记》的时候,我对萧何非常佩服,因为如果没有萧何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刘邦。刘邦出去打仗都是萧何在后方,当刘邦和项羽对峙的时候,萧何能够提供各种后勤方面的保障。但同时他又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汉承秦制”是萧何提出的,并不是刘邦。我当时看到的资料记载也是萧何把所有秦朝的资料典籍都拿走了,项羽没有得到这些东西,他也未必想要这些东西。所以萧何在“汉承秦制”和帮助汉朝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封建制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是真正的精神领袖,刘邦更像是一个代言人。萧何在众多的大臣中是唯一有资格在进宫的时候穿鞋带剑的,这说明他有极高的地位。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有时候会想,当萧何去追杀韩信的时候,他见到韩信的那一刻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这个恰恰是我最关心的事情。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不是变节,而是他在变节的时候依然还有良知,这种良知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撕咬他,这才是最大的痛苦。我不知道在所有知识分子中有多少是属于萧何这种的,像萧何这种人我依然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只是可以感受到他很挣扎,他在挣扎着让自己去适应这种权力生态,让自己不去违背这种生存法则,这种东西基本上只在中国有。当皇后不见萧何的时候,他就要求去见皇上,当他跪了一天皇上依然不见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已经土崩瓦解。他的信仰、人生的支柱不是独立的,而是依附在刘邦身上的,他觉得刘邦给了他这样的空间,但当刘邦说你没有这样的空间了,他的一切信仰都分崩离析。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人的人性像金属,他们在被扭曲的过程中是需要力量的,而有些人的人性就像面条一样,可以任意扭曲。
陆川:我觉得张良就特别像面条,张良特别明白这些东西,他不觉得一定要坚持些什么。但我在这部片子里有些东西没有拍,萧何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和刘邦的理想是一样的,帝国官僚制首先是萧何的理想,其次才是刘邦的理想。萧何在杀韩信的时候,他面临的选择可能是我是做一个人,还是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建立帝国伟业,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帮凶,他只是在做一个正常人还是一个“股东”之间做一个抉择。当时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最后没拍出来是因为,如果再拍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刘邦、项羽、韩信三个人还没搞明白,如果再加一个萧何那就更难把控了,所以后来在这条线上我们就没有走得太远。但在探讨知识分子这件事上,事实上表面上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秘密利益分配的“股东”,所以他们面临的选择就是做一个“人”,还是一个秘密利益分配的“股东”,这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所以,这部电影真的让我有一种Hold不住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次拍电影都很下工夫、很用力。但很多导演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往前走,电影让人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但也没什么特别值得回味的东西。他们会用成熟的技术来规避审查制度。可你好像还没有掌握好这种生存术。
陆川:我是一拍起来就忘了,我确实比较任性,无论是拍《南京!南京!》还是《可可西里》,真的是没有想这些东西。覃宏对我也特别宽容,不过问太多这方面的事儿。我们两个人很奇怪从来不聊这方面的事儿,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和覃宏都不够专业和懂事儿,这次算是一个教训。虽然是这么说,但我很怀念这样做电影,我怕有一天我真的开始懂事了就会失去这些东西。事实上,这个跟头摔得太大,逼着我已经开始懂事了,两年的时间,近1亿元的资金压在那儿,当时也借了将近600万元,为了还剧组工作人员两个月的工资,自己的公司也一直在垫钱。前段时间,600万元的债到期了必须还,我就只好抵押了一套房子,先还了一部分。除了第一部戏是被人领着走的,接下来的三部戏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样的状态我真的很怀念,觉得自己挺对得起这12年的,我很高兴自己电影的青春期是这样度过的,我希望自己不要把这些东西丢掉。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你将来再拍电影,一定会想到这个过程,这次的教训会不会让你在未来拍电影的时候会失去某些东西?
陆川:所以我觉得冯小刚还是很值得尊敬的,他已经那么成功,还会来触碰这样敏感的话题,这对我来说很有触动,因为别人的历史也会成为自己的历史。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拍像之前的四部戏一样让自己有特别大的冲动同时也特别喜欢的戏。未来的事情真的不好说,但我觉得我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去回忆这些事情,可能一年之后我们再坐下来聊这件事比较能说得明白。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题材去拍,这样才有意思。
相关报道:
- 姚晨片场过生日:曹郁抱儿子现身 陆川送祝福(图)2014-09-09
- 陆川大礼贺寿星姚晨 鬼吹灯分镜图首曝光2014-09-09
- 《鸟巢·吸引》全面启动 陆川有望回归2014-05-21
- 陆川首承认与秦岚分手 曾想挽回恋情2014-03-12
- 曝陆川秦岚分手 男方要结婚女方不愿安定2013-10-28
本类最新
本类最热
科技视界
要闻推荐
今日视点
热点专题
新闻图片
- 新闻排行
- 评测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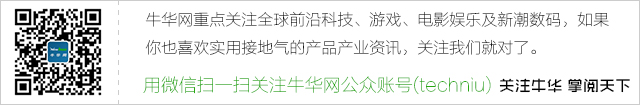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 32132202000111号
苏公网安备 321322020001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