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电影多元素组成

迪斯尼出品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史崔特先生的故事》
·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
无论是《逍遥骑士》中的哈雷摩托车、《末路狂花》中的蓝色敞篷蓝鸟,还是《落叶归根》中的重型大卡、《后会无期》中的改装POLO车,一方面推动着剧情发展,给主人公制造各式各样的麻烦,又符合戏剧化原则,迎合了观众喜欢影片的主人公陷入困境、在泥潭中挣扎的喜好,同时也是人物性格特征、身份背景与社会表征的显现。
《逍遥骑士》中的哈雷摩托是狂放不羁的人格象征,著名行为艺术家严路便是哈雷的忠实粉丝之一,他曾这样描述:“对我而言,赛车像是一首交响乐,精细严密,需要很多的配合协作。而骑哈雷则更为惬意,当它进入你眼帘的那一刻,你总是会想起年轻时走天涯,四海为家的梦想。骑上哈雷,就等于完全释放自己。这更像是一首乡村音乐,是一个人怀抱吉他,走走停停的流浪旅程。”毫无疑问,哈雷摩托成为男性的至爱之选;《阳光小美女》中的黄色大众汽车,则是The Beatles乐队在《Yellow Submarine》中唱到的六七十年代美国人自由的象征与中产阶级家庭的证明,而这辆汽车在行驶途中的几次抛锚,也暗示着美国理想的起伏与消亡。

《不毛之地》1973年
·结伴同行的旅人
落单的旅人总会找人结伴而行,打发旅途中的寂寞。聪明的导演和编剧通常也会把两个或多个人凑在一起,藉他们之间的互动制造出更多的戏剧效果。在公路片中所出现的结伴同行的人,或与主人公从初始地一道出发,或半路匆匆相遇又匆匆离场,他们形象不一、身份各异,有淘金者、流浪汉、旅人、故友,还有因伤心而逃避的人。但其中“亡命者”这一形象往往最为常见,也最受观众的欢迎。
如《后会无期》中钟汉良饰演的阿吕,虽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亡命之徒,但其设定于行为也为原本较为平和的剧情下了一剂猛料,丰富角色类型之余,也创造出更强的情节冲突;另一方面,旅途的过程本身足够精彩,加之沿途中突然出现的危险人物,也能够营造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又有定时炸弹随时引爆”的戏剧效果,让剧情本身拥有更大的张力——公路电影能把不同类型片的成分拼凑在一起,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如果把公路片比作导演或编剧下的一盘棋,这些旅人的角色便是随时增添的棋子,随时反射出执棋者的各种小心思,既可以调动观棋者的注意力,又能够把握最终剧情的走向,组成最完美的棋谱。

·永远无法顺利到达的目的地与贯穿始终的公路
大多数公路片往往被看作是电影中的“异见者”,因为它并非全然乐观,或者可以说,悲观或者忧伤是公路电影的主旋律,这种天然的“不同意见”使得公路片具有一种别样吸引力。基于影片的可看性,主人公如同做任务升级一样的不停遇到事故上与心灵上的种种困难,车子抛锚、财物遗失、旅伴去世……我们也很少发现一部从头到尾始终热情洋溢、昂扬乐观的公路片,如果要同很多小说一样,给公路片加一个标签,那么大多观众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怅然若失”。就像《阳光小美女》结尾处祖父的去世,《落叶归根》中老赵将老王的骨灰带回乡却发现三峡移民使“故乡”已不复存在,都给看上去成功的旅程画上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公路”是充满隐喻和象征的一个元素,它更多的预示了另外的一种人生理想或乌托邦:一条充满黄沙、尘土和岩石的道路;一个空旷之地与世界尽头。似乎只有在那里,内心中最真的、最自然的、最向往的,或是记忆中最深刻的才能够被找到。因而无论电影怎样变化,公路都贯穿所有公路片的始终,由原本简单的背景不断上升为影片里的最大隐性角色。
中美公路电影互异性

《落叶归根》与《逍遥骑士》作为中美早期公路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创始者”与“继承者”——背景与主题差异
任何外来物种在经过长途跋涉进入异邦时,都无法摆脱本土化的过程。公路电影作为在中国电影领域里初露头角的舶来物,无论在影片的叙述主题上,还是在精神格局上,都具有鲜明中国电影的特色。近三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城市大量兴起,土地逐渐缩小,由乡村而城市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突出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中国人一直走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路上这种漂泊是这类人的基本生存与精神状态,因而中国现有公路电影一半以上均是以农村或乡镇为背景,人物之间的矛盾也大多来自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
与美利坚民族的精神流浪相比,中国社会中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的流浪更多了几分无奈。“我没想到《在路上》卖得这么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现在年轻人爱这本书。凯鲁亚克这个人整天在东海岸、西海岸来回折腾,没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干,有书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点乱,还吸毒品,年纪很轻就死了,46岁吧。”《在路上》的译者王永年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并不存在以美国骑士精神为代表的公路片的土壤。
在面对现实的残酷,与家园温情的失落中,中国的公路电影集中反映了电影创作者内忧外患的生存困境,他们拼死挣扎于理性的道德规范和非理性的欲望本能之间,在迷惘与无奈中苦苦寻找自己的心灵家园,呈现出一种精神的漂泊,而非本能的冒险与逃亡。
·“巨石”与“瓷片”的碰撞——影片数量受众与风格差异
“国产片连续数年票房份额超过进口片”的公告与统计数字上的再创新高,并不能掩饰越来越缺乏活力的中国电影,侧重表达自我的艺术电影,无法与更为广泛的观众打成一片。大多数第六代导演作品比较受艺术院线认可,在粗放发展的国内市场影响很小。
从影片风格来比较,中美公路片最大的不同是美国整体趋向硬朗,而中国总是在小文艺上寻求特别。《无人区》、《后会无期》等都是如此,追求画面精致与故事伏笔,以及对台词的苛刻;而美国只要“人的真实”,追寻就是为了自己活着,更加注重态度与自身看法的表达,将一个大事件永远作为最重点贯穿始终。
作为公路片始祖的美国,其“公路片”已成为一块百撼不倒的金字招牌,将类型电影中这一类别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长期发展中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观众群体,其吸金能力不可小觑。而中国电影从业人员普遍缺乏对类型片的创作实践与细致分析,大多表达某几个导演、几个人对社会的看法,缺少对最普遍的一个观众接受层面的考量,使得电影工业得到无法良性循环,公路片等类型电影再次陷入困境。
·“大杂烩”与“蛋炒饭”——融合元素与电影类型差异
将公路片按照电影类型仔细分类,不难看出美国公路片不仅胜在数量众多,并且在其元素与类型上也表现突出:犯罪、动作、惊悚、悬疑、冒险、剧情、爱情、喜剧各色荟萃,层出不穷,欧洲与澳洲的公路片甚至在歌舞片(澳大利亚1994年《沙漠妖姬》)和科幻片(德国1991年《直到世界末日》)方面有所补充和拓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公路片则给人一种“标准XX+公路双料炒饭套餐”的感觉,将某一元素与公路元素相结合,影片成败不在“公路”运用得如何,而体现在具体加了什么料和它一起下锅上,喜剧与爱情便是其中最常用的应景元素。《人在囧途》系列的成功,并没有让公路片这一类型电影家喻户晓,而仅仅停留在让人们记住了“傻根儿”染了个金毛,多了个新朋友这一层面上。
·谈中庸元素与思乡情结的逆袭
在大部分尤其是以逃亡为主题的中国公路片中,当人物一般需要面对现实的残酷和重量超越了本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时,才可能开始遮掩,从而产生开始公路逃亡。而在这漫漫的逃亡路上,由于中国人思乡情结和中庸文化的存在,逃亡并不能获得多大的宽慰和安心,相反巨大的恐慌和寂寞可能侵袭而来。因此在逃亡的路上人物并不能得到释然,唯有选择面对或是妥协,然后妥善的解决它们,于是才会让心得到解脱,因而中国公路电影的人物选择一般最终归于社会传统。
如《走到底》中,茉莉和王宏伟也来到阿冬家,才得知阿冬已经在逃跑途中被警察击毙。茉莉和王宏伟知道警察在寻找自己,决定不再逃避,开始新的生活,反映出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大团圆结局。当然,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不同地区版本剪辑的选择上,如刘青云主演的电影《神探》,其内地版本将粤语版结尾的亮点一笔抹杀,匆匆安上了符合社会道德正义标准的生硬结局,这也不得不说是内地审片的缺憾之必然结果。
相关报道:
本类最新
本类最热
科技视界
要闻推荐
今日视点
热点专题
新闻图片
- 新闻排行
- 评测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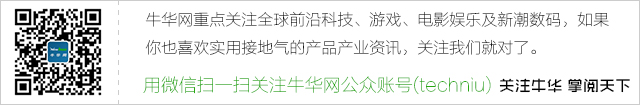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 32132202000111号
苏公网安备 32132202000111号